
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,一列银灰色超速试验列车停放在厂区的铁轨上,这列台架试验速度每小时达到605公里的列车,被命名为更高速度的试验列车。
实际上,这项试验早在两年多前就已开始,为了这次试验,南车四方公司经过七次方案讨论会。
参加试验的电气开发部部长焦京海最近回忆说:“100-200公里时一点担心都没有,车速上了550公里以上心情开始激动,到600公里时就开始有点紧张了。”试验止步于605公里,是因为制定的试验目标为600公里,“试验台建设时是按600公里设计的,再往上冲速度,担心对试验台不好”, 高级主任设计师李兵解释说。
当时速提升到605公里的时候,试验没有马上停止,保持速度运行了10分钟,这相当于在地面上行驶了100.8公里。
技术难度比飞机高
“高铁就像一架飞机在不停地起降”,中科院力学所杨国伟研究员这样说。杨国伟创立了跨声速非线性气动弹性研究,为中国高铁与大飞机研制提供空气动力与气动弹性的技术支撑。
“坐飞机最危险的是起飞和降落,因为地面效应包括建筑、风对飞机的激扰,所以,飞机设计的难点在起和降的过程。而高速列车始终在地面上高速运行,从空气动力学车与空气相互的作用角度,既要考虑地面对列车的强激扰,也要考虑到高速运行状况下气流激扰。波音737的巡航阻力系数约在0.028左右,6辆编组试验列车整车阻力系数约为0.48左右,所以说更高速列车比飞机在天上巡航时的技术难点要复杂得多。”杨国伟说。
民用飞机每小时飞行距离800-850公里,中国研制的更高速试验列车设计速度在每小时500公里以上,与目前在线上以每小时380公里最高时速运行的CRH380A相比,技术的边界条件必须清晰。
“空气动力学性能的受轨道不平顺影响,振动激扰响应不断加大,如何保证列车高速运行的安全性;如何保证舒适的乘车环境;比提高速度更重要的是能够很好的停下来。” 试验现场指挥梁建英说。
列车运行的阻力,包括车轮与轨道摩擦的机械阻力和车辆受到的空气阻力。高速下制约速度的抗衡者是空气,“当列车以每小时200公里行驶的时候,空气阻力占总阻力的70%左右,和谐号CRH380A在京沪高铁跑出时速486.1公里时,气动阻力超过了总阻力的92%,如果跑到500公里以上,95%以上都是气动阻力了”,李兵说。空气阻力和列车运行速度的平方成近似正比关系,速度提高2倍,空气阻力将增至4倍。正是这个平方关系,让设计师绞尽脑汁。
空气阻力受三大因素影响,一是车头迎风受到正压力,与车尾受到的负压力间产生的压差阻力;二是由于空气黏性作用于车体表面的摩擦阻力;三是列车底架以及列车表面凹凸结构引起的干扰阻力。
工程师们为降低空气阻力,应用仿生学和空气动力学理论,创作了100多种头型概念,优选构建了80余种三维数字模型,开展了初步空气动力学仿真,比选出20个气动性能较优的头型,进一步进行气动优化,制作出1:20实物模型,根据仿真数据和美观效果,最终制作五款1:8头型分别做了风洞力学试验和气动噪声试验,名为“箭”的头型被选中,其气动噪声、气动阻力参数最优。“从气动性能来讲,‘箭’与民航客机是可以PK的。”李兵说。
让数百吨重的更高速列车在线路上飞跑,除了减少气动阻力外,加大牵引能力是另一个关键。“六辆编组更高速试验列车牵引总功率可达到21120千瓦。正是有了我们自主开发的大功率牵引系统,才有高速试验列车实现台架试验605公里/小时的可能。”焦京海说。
大功率的牵引传动系统的技术研发,具有强大的技术扩散效应,除列车之外可应用在其他制造领域。“大功率的牵引传动系统技术具有很好的外延性,除轨道交通领域以外,大功率的牵引传动系统在很多工业传动领域都有很广泛的应用,比如轧钢系统、船舶推进系统、石油钻井、电力系统等等。”南车时代电气技术中心主任荣智林说。
高速列车运行依靠电能,是由受电弓与接触网接触完成的,这个过程被称为“受流”环节。这项技术也是迄今为止技术专家们最关注的技术之一。“双弓受流”技术曾经是困扰工程技术人员的一个技术难点,“现在看来这个也不太像技术难点了”,梁建英说。“车辆在高速运行时,前弓在取电滑过接触网时,会形成一个激扰波,导致后弓的离线可能性加大,影响车辆的牵引性能。如何保证后弓受流的稳定性,这是技术上的难点。但是现在看来,已经不存在了”。
追求更快速度
速度是技术发展的综合实力。如同中国“两弹一星”的研制,举全国之力,近万名科研技术人员参与了高速列车的技术创新。“试验列车的速度还只是实验室内的数据,实际的线路数据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,我们希望有个高的速度值,让全世界都能进一步了解中国的高铁技术和产品水平,其中的过程需要踏踏实实去做,而决不能急于求成。”梁建英说。
“时速605公里是试验台上跑出的,不是在线路上的数据,实际的线路试验还需要一系列的考核。”李兵说。2007年4月3日,法国TGV在线路上创造574.8公里/小时试验最高速度,目前为止尚未有新的记录刷新。2010年12月京沪先导段试验蚌埠-枣庄,CRH380A达到最高时速486.1公里,这个速度尽管是运营试验速度,它有别于法国TGV的纯粹试验速度。就运营试验的速度值来讲它是世界上最高的。
2011年,“7•23”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后,中国高铁开始了对更高质量目标的追求,其中包括安全性、可靠性、舒适性等。事实上事故并不是缘于车的质量,但是这次事故却对中国高铁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。所有的铁路人,包括南车四方的技术人员都在反思,那就是如何更好、更稳健地推进国家的高速铁路事业。试验列车的研制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。它以CRH380A新一代动车组技术创新成果为基础,遵循安全可靠的运行目标,针对系统集成、车体、转向架、牵引、网络控制、制动系统进行了诸多技术创新,实现了碳纤维材料、镁铝合金、纳米材料、风阻制动系统等一系列新技术、新材料的装车试验验证。整个列车的研制历经了两年多的时间。
试验列车完成在实验室的测试后,在厂区内一条3.7公里的环形试验线上进行了一个月可靠性试验,运行里程约1000公里。受线路条件限制最高速度不得超过时速30公里,“对整车、系统及部件完成了初步可靠性验证”,工程师告诉记者。
多项新技术有待验证
高铁,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,而更高速列车则是中国创新能力的又一标志性作品。工程师与科学家渴望上线试验衔接试验台的验证结果,更加深入地探索超高速列车三大核心技术理论,即轮轨技术、空气动力学性能与弓网关系。
对工程师而言,诸多项设计是无法在台架试验中完成的,更高速列车的三项核心技术有两项无法验证,即空气动力学性能与弓网关系。
比如,台架试验在室内完成,缺少了风,则无法完成空气动力的试验。“更高速列车首要的验证是车的阻力特性,牵涉到能耗;其次是升力特性,涉及到脱轨系数;第三是脉动力的大小,涉及到列车的安全性。还有就是交汇瞬时风的阻力,以及安全的避让距离。从理论上讲,目前已有的公式对400公里与500公里的车应该是适用的,就研究和印证来说,这些都是需要通过线上试验进一步验证。”杨国伟说。另外,即便是双向滚动试验台,也无法完成受电弓与接触网的受流试验。
对做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而言,他们希望验证共性关键技术的基础理论机理。以脱轨系数为例,车辆运行时,在线路状况、运用条件、车辆结构参数和装载等因素最不利的组合条件下可能导致车轮脱轨,评定防止车轮脱轨稳定性的指标叫脱轨系数,这个系数越大越容易脱轨。
根据国际标准,0.8作为脱轨安全性的指标。“但是我们对高速列车试验时发现,列车在线上以480公里的速度,脱轨系数只有0.1-0.2左右,远远小于0.8。如果以每小时550公里的速度,实际运行时的脱轨系数是多少?它涉及到高速基础力学的研究。全球范围的科学家们一直希望破解脱轨系数之谜。”转向架高级工程师马利军说。
带动行业发展
本世纪是高铁的时代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表示,“没有理由让欧洲和中国拥有最快的铁路”,奥巴马强烈意识到,高铁将是重塑美国全球竞争力的技术制高点。“技术上一定是要抢占制高点,谁有抢占技术的制高点的能力,谁就有带动行业发展的能力。以技术的先进性驱动市场的需求,这是全球市场经济竞争的规律。”梁建英说。
2007年法国TGV创造“全球第一速”,以抗衡德国磁悬浮列车抢占市场的挑战。“法国正是因为在路上跑了570多公里,给世界各国明确的信号,我的技术是可行的。从此之后,世界高铁市场法国成为佼佼者。”杨国伟说。中国高铁驶向世界的脚步正在提速,说明高速仍旧是趋势。探索500公里以上超高速列车的技术,既是一项前瞻性的研究,也是拓展国际市场的技术储备。
技术的成熟需要积淀,而市场的拓展则是瞬间的外延。中国高铁从2004年开始,经过9年的时间,从引进、消化、吸收到如今技术的全面领先,更高速试验列车的研制是技术纵向发展的制高点,只有掌握技术的制高点,才能够使技术纵向与横向相互传递,覆盖市场的面积递增。“这个试验列车它的基础是在CRH380A技术向上拓展的,而城际列车则是向下的拓展。高铁这么多年的技术创新,其技术先进性已经向上下游产品传递。”梁建英说。
对技术的追求并未停止。为了更好地理解空气动力学的作用关系,南车四方股份公司正在计划筹建一个小规模的风洞实验室。“虽然我们是一个工程单位,但是我们需要自己去突破,掌握和积淀一些新技术,想为以后留下点什么。”梁建英对记者说。
对更高速试验列车的线路验证,国家有关方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,列车的上线试验工作已在全面展开,列车的各项技术性能将在线路试验中得到进一步验证。整个过程将分阶段实施,会一步步获取各种技术参数。“我们期盼它有非常好的表现,让全世界都进一步了解中国高铁技术。”工程师们说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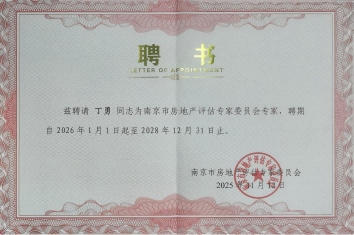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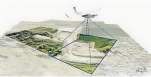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苏公网安备32010502010886 号
苏公网安备32010502010886 号